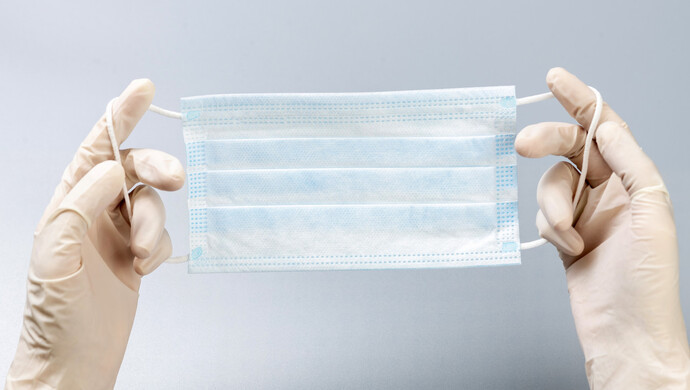
在瘟疫与人类相伴的历史中,隔离治疗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养内避外”的防疫观念即蕴含了通过隔离来阻断外界感染的思想。欧洲14世纪“黑死病”爆发,此后以鼠疫为代表的烈性传染病的威胁始终存在,针对流行病的防护被认为非常重要,隔离制度即为其中一项。防疫隔离制度的目标在于让传染病患者和疾病易感人群受到照料,从而在疫病流行期间防控病菌传播,重构社会和空间秩序。近代中国将隔离治疗作为防疫制度之一种,始于清末东北鼠疫。在防疫制度的法制化进程中,隔离治疗构成了传染病法规的重要原则,其强制性特征通过防疫警察、专业医生等执行者得以实现。隔离机构也逐渐摆脱临时应急场所的定位,进而成为公共卫生的空间和物质象征之一。
一、清末东北鼠疫:隔离制度的近代开端
1910年10月,东北爆发鼠疫,且波及关内许多地区,至1911年4月疫情渐熄。清末东北鼠疫造成六万余人死亡,死亡率极高,人们闻鼠疫而色变,交通中断更直接导致市井萧条,商业不振。面对这场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等。同时,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了著名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以伍连德为代表的中外鼠疫专家们确定了此次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型鼠疫,然而当时中西医界对于鼠疫治疗皆无有效技术手段,只能依靠隔离病人和阻断交通等强制措施来控制疫情传播。
当时东北涉疫各地均设立隔离医院或疑似病院,如哈尔滨、安东(今丹东)、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处均设有隔离机构。以《奉天防疫事务所章程》为例,第一条即规定:“本所之宗旨专为患疫之家族避疫而设,其隔离期限必须七天,方可放归。”隔离所内分男女两房,隔离医官每天诊断两次,判断隔离者的健康状态,无论何种病患皆送入“休养室”,发热者的样本直接送入微生物试验部检验,如果确诊为鼠疫则直接送入“避病院”,并对其住处严行消毒(《盛京时报》1911年2月16日)。由于疫情多沿铁路或水路传播,各口岸亦设立“隔离所”,派人严查。如安东为预防疫情,预先在太平沟、安子山等口岸设立隔离所,“无论汽船、帆船抵口所装客人一律送入隔离所诊视,如有病者即送医院调治,以期痊愈,无病者留验七日,再行放行到埠”(《盛京时报》1911年3月7日)。
左右两图分别为清末东北鼠疫时期哈尔滨傅家甸第一时疫医院和第二疑似病院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会议明确了此次东北鼠疫的病源地和病源物、传播途径、病状诊断,认定了国际通行防疫方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最终通过了决议条款45项,其中提出的种种举措确定了此后防疫制度的基本原则,即隔离病人与阻断交通(《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奉天全省防疫总局1911年)。如第十一项甲“患疫者、疑似病者及病者周围之人,皆使之隔离,其不从者,则强迫之。又患疫者、疑似病者及病者周围之人,皆使之带合法之呼吸囊,以免传染”。对于隔离机构的类别亦有详细规定,如第十三项规定预先建造接收确诊病人的疫病院,第十四项关于接收疑似病人的疑似病院,第十五项为接触疫病者的留验所。疫病院、疑似病院和留验所三种隔离机构,针对不同防疫对象而设,体现出当时隔离治疗的细分化与科学化趋势,只是在当时的防疫过程中,这些隔离机构大都临时征用房屋而建。
隔离治疗被确定为疫病发生时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有论者意识到强制隔离治疗在现实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如谭其濂肯定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决议条款中隔离概念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建议稍作改变。西医已经证明肺鼠疫的传播媒介乃病人痰中之飞沫,却无法施治,染病者无异于被宣告死刑。此时若对病人隔离治疗,令其举目无亲,每日面对身着防护衣、面戴口鼻罩的防疫人员,病人很可能因悲伤情绪而致病情轻者变重,病情重者变危。因此,谭其濂建议隔离医院“不妨准病者亲属入院探视,如其为幼孩,须人保抱,亦不妨准其所亲一人留院侍疾,惟须严订院章,使其不至害及他人”;他甚至还建议病人可自行延聘合格的医生入院协助治疗。其目的在于消除病人及其家属的顾虑,使其主动上报病情并接受隔离(谭其濂:《癙疫》,商务印书馆1918年)。
1918年1月初,山西爆发鼠疫,蔓延七十余日,至3月中旬乃扑灭。时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迅速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总局。与谭其濂类似,阎锡山参考了《东三省防疫纪事》及《万国鼠疫研究会条款》,虽然接受了隔离病人和断绝交通的原则,但是对于隔离所的设置仍有疑虑:“若设所隔离,不特人民之疑惑滋多,致生谣喙。且父病不令子侍,夫病不令妻侍,大反乎家族主义。揆诸风俗习惯,甚难实行,强而行之,终恐激成事变,致生反动,愈难着手矣。”(周成:《地方自治讲义》第一册,泰东图书局1925年)强制隔离治疗有悖于家族主义和风俗习惯,很难为民众所接纳。解决之道在于允许家人进入隔离病室陪护,只要侍病者戴上口罩即可。进而论之,无疫区只需断绝交通并执行七天隔离,以度过潜伏期;有疫区只需佩戴口罩,以切断病菌进入口鼻的路径。不论是医生谭其濂还是督军阎锡山,都采取了一种折中式的隔离思想,吸收了戴口罩阻隔飞沫传播的新医学防疫思想,同时,试图将生疏的隔离环境转化为家庭式的隔离情境,强调亲友照护与陪伴。在他们看来,这种折中主义更能鼓励民众主动报告疫情,从而实现“防”疫之目标。
二、防疫法制化:隔离法规与防疫警察
以清末东北鼠疫和1918年山西鼠疫为代表的传染病防治的地方经验,显示出疫病“预防”的重要性。防疫制度作为国家卫生治理的重要手段,自民国初年开启了法制化的进程。1916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民国时期第一部全国性的传染病法规。其规定了八种法定传染病,即虎列剌(霍乱)、赤痢(痢疾)、肠窒扶斯(伤寒)、天然痘(天花)、发疹窒扶斯(斑疹伤寒)、猩红热、实扶的里(白喉)、百斯脱(鼠疫),以及总体的防疫原则与措施。1928年9月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与1916年的条例几乎如出一辙,只是在1930年9月修订时增加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脑膜炎)为第九种法定传染病。“隔离”构成了中国近代几部传染病法规的关键词之一,涉及隔离对象、隔离场所以及疫情报告制度等内容。
《传染病预防条例》,1930年
在隔离对象和场所方面,1928年的条例第三条规定:“人口稠密各地方应设立传染病院或隔离病舍”,传染病院为常设机构,隔离病舍为临时机构;第十条“凡经该管官署认为传染病预防上之必要,得使患传染病者入传染病院或隔离病舍”,第四条“当传染病流行或有流行之处时,地方行政长官得置检疫委员使任各种检疫预防事宜;于舟车执行检疫时凡乘客及其执役人等有患传染病之疑者,得定相当之时日扣留之;于舟车执行检疫时发见传染病人得使就附近各地方设立之传染病院或隔离病舍治疗”,这两条分别指向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
在疫情报告制度方面,对于确诊病人或死者,医生须在12小时内上报辖区官署;对于疑似病人或病人接触者应延聘医生诊断,医生负责指示清洁及消毒法,并于24小时内上报。医生诊断病人或检查尸体后,不上报官署或报告不实者,处以5至50元罚款;其他病患不上报、报告不实或妨害他人报告者,处以2至20元罚款。
在这里,法律条文关于隔离病人及其家属以及阻断交通的规定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时人在解释传染病条例时指出:“虽制限个人之自由,妨害公众之利益,亦所不惜。”(周成:《卫生行政讲义》,泰东图书局1925年)由于个人并不具备使传染病人与社会隔绝的权力,因此,当有传染病发生时,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公权力,必要时执行强制隔离,以预防并制止传染病的流行。防疫警察因此被赋予合理性与合法性。
所谓“防疫警察”是卫生警察之一种,“乃为保护公众身命安全,而预防扑灭有传染性之疾病的警察作用也”。其职责在于执行《传染病预防条例》等卫生法规中要求地方官署施行的各项防疫举措,比如在急性传染病方面,令患传染病者入传染病院或隔离病舍接受治疗;对传染病死者尸体施行消毒,经医生检查及官员认可后于24小时内殓葬;对传染病患者同居之人或其他疑似受感染者,施行清洁并消毒,并可强制其入隔离病舍;对传染病患者之家属或近邻,可隔断交通等(张恩书:《警察实务纲要》,中华书局1937年)。
卫生行政是现代国家权力的实践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卫生与警察两个部门的分合轨迹。防疫警察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卫生”由保卫个人生命的传统意涵向国家卫生现代性转变的表征。传染病法规付诸实践的强制性通过防疫警察的职能得以实现,专业医生则依据医学细菌学的实验结果确定了特定传染病的隔离时间,从而进一步促成了防疫隔离的制度化和标准化。每种传染病的具体隔离时间并未写入《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如1930年的条例只是在施行细则中规定了感染者同居之人或其他疑似病人按照条例规定进入隔离病舍消毒并隔离数日(最短为白喉3日,最长为伤寒15日),感染者及其接触者的实际隔离时间大都由卫生部门或隔离医院自行规定。1934年3月,上海工部局公布了各种传染病症的最少隔离时长,提醒学生家长、工人雇主予以注意:
表格中诸如天花、猩红热、白喉、脑膜炎等传染性极强、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原则上要求病人入院隔离,其他传染病则可采取居家隔离的方式隔离数周,接触者亦须居家隔离,只是时间较短。此外,对于某种传染病的隔离时间并无定论。以猩红热为例,进入隔离医院后一般须住满五周,而学生、医护、机关或公司职员等日常与大众接触者,则须住满六周。时人另有隔离四周或八周的说法,不过隔离期限并非唯一考量,应以耳鼻喉部位的炎症是否消退、皮疹是否脱尽为标准(天津《益世报》1934年3月13日)。最少隔离时长的规定亦呈现出隔离治疗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特征,并促成防疫法制化的进一步完善。
三、隔离之所:设想与困顿
中国古代已有各种疫病隔离机构,如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唐代的疠人坊或疠所、宋代的病坊和安济坊等。欧洲近代以后逐渐出现一些永久性的防疫医院,通常建在乡村里或岛屿上。城市近代化带来人口增长与聚居,医学细菌学进一步证实了传染病的发生机制,这些都使得隔离医院成为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10月国民政府编印的《全国防疫计画书》中,规定各市县至少建立一所传染病医院,医院至少可容纳二百人,内部应包括消毒室、门诊室、隔离病室、诊断实验室、医护住宅等设施。建筑可暂用旧式公有房屋加以改造。
以上海而论,上海近代早期的西医院大都设有隔离病房。较早的专门隔离医院有1904年成立的工部局隔离医院、1910年的中国公立医院(即红十字会时疫医院)、1914年的工部局华人隔离医院等。1930年的《工部局卫生示谕》描述了隔离病人的基本流程:凡感染疾疫危险病症者,皆可租借工部局的病人运送车(汽车),送至工部局华人隔离医院,接受免费治疗。病人运送车免费运送隔离病人,每次运送病人后皆消毒。传染病患者住处亦可请求卫生处免费消毒。
上海工部局病人运送车,1923年
华人隔离医院分为“通房间”和“包房间”两种:通房间每间病床八至十张不等,除血清注射外,其余医药费全部免除;包房间每间病床两张,准许带仆役一人,收费较高。病人入院后先行消毒,特别是病人衣物的消毒,而后根据病情给予治疗。隔离病室按传染病主要分为四类,即猩红热、白喉、天花和脑膜炎前述这四种要求强制入院隔离治疗的传染病。院中有主任医师一人、看护十四名、女看护长三人(皆为西人)。每天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家属探望病人时间。家属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不准进病房,只许隔着窗子说话(《同济医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3年)。
1929年春,上海脑膜炎流行。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发布通告,要求市民自动隔离,外出时可戴纱布口罩,不要聚集,停止集会(《民国日报》1929年4月13日)。工部局则规定,脑膜炎患者应即刻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然而,一位读者在5月19日的《民国日报》上撰文抨击工部局隔离医院竟然不收治脑膜炎病人,理由是病人是法租界居民。这名读者认为医院当局对于时疫等急症不应设有管辖区的限制,而应以救人生命为前提。事实上,由于当时脑膜炎疫情严重,工部局隔离医院已人满为患,因此只能接收公共租界的病人,来自法租界及华界的病人则一律拒绝。法租界病人原则上应送入广慈医院,闸北、南市病人则分别送入中国公立医院和上海医院(《时事新报》1929年4月8日)。当然,大部分脑膜炎患者会选择或者说只能居家疗治(《时事新报》1929年4月8日)。脑膜炎患者被医院拒收,虽然存在管辖区的问题,但背后乃是防疫隔离医疗资源不足所致。
左:广慈医院隔离病楼,1930年;右: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1914年
时沪上西医庞京周指出:“上海市内尤感觉缺乏而急于要提倡的,乃是传染病医院。”当时可接收传染病人的医院主要就是上述几家隔离医院,大部分感染者或疑似患者皆居家治疗,其中一些人会延聘医生到家中。按照传染病法规的要求,医师有上报传染病的责任,但是实际却难以执行。庞京周认为,病家对于送医院去隔离都有毛骨悚然之感,医生对于病家有三种态度:热心的医生不管病家是否愿意,上报工部局把病人硬接去;略为消极的医生则顺从病人的要求,隐瞒不报,做着出诊的生意,冒险在病人家中施以治疗;最消极的医生则对病人完全放弃,“更不去管他们传染不传染”。而最为重要的是,即使所有病例全部按照要求送入隔离病院,上述几家隔离医院也无法全部收治(庞京周:《上海近十年来医药鸟瞰》,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
鉴于此,按照医学科学的方法居家隔离就变得十分紧要。当时有关家庭卫生的书籍中有大量内容教授如何在家庭条件下设置防疫隔离环境。诸如猩红热等传染病一经发现,必须立即将病人隔离,“隔离之最妥方法,莫如住于医院,偶或不得住医院时,家中亦可勉行之”,“隔离之主要点,即病人住室须单独分开,与其他房屋无甚联络……问询者与送物者,均不得入内,只能在门口讲话或传递物件,以不接触屋内一人一物为要”(《国民卫生须知》,中国卫生社1935年)。居家隔离的重点在于开辟专供病人或护病者使用的独立空间,且须避免接触传染的发生:“病人所居的病室,除护病者外,无论何人,不准入内,谓之隔离室。室内用品,除可以煮沸、烧毁或洗擦者外,其他不相干的装饰品,一概移去。……室内空气,必须流通。最好接连病室处有浴室一间,及护病者的居室一间。此三室与他室不相交通,而专供病人与护病者的应用,实为最妥善的布置。”(葛成慧:《家庭医事》,正中书局1937年)
隔离治疗作为防疫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近代防疫制度形成之初即被作为重要的经验与原则写入传染病法规之中,隔离场所的建设逐渐成为公共卫生与防疫制度的重要目标与实施途径。隔离治疗所蕴含的强制性特征通过防疫警察和专业医生来实现,但是隔离医疗资源不足确为现实中遭遇的困顿。即便是在上海这类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在大规模疫情来临之际,隔离医院仍不敷应用。加上民众惧怕去隔离医院的心态,以及医生出于利益考量的瞒报,当时能够接受隔离治疗的病患比例相当之低。此外,由于基本卫生常识的缺乏,病人及其家属的居家隔离之做法,与阻断病菌传播之目标常常背道而驰(《时事新报》1936年2月7日)。
防疫实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病患及其接触者、医护人员、卫生当局等各个方面,如何在多方互动关系中实现强制原则与折中主义、入院隔离与居家隔离的平衡,如何实现防疫医疗资源的充足准备与合理利用,如何在保障防疫事业有效进行的同时合理降低防疫隔离所带来的个人身体被剥夺感,这些始终是近代的防疫隔离制度制定者与实施者考虑的关键问题。
责任编辑:延菁菁
版权声明: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本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85 8629 6259